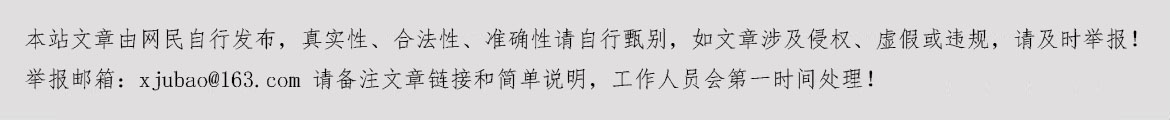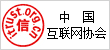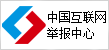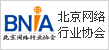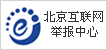恒信网是领先的新闻资讯平台,汇集美食文化、综艺娱乐、热点新闻、商旅生涯、生活百科、体育健康、等多方面权威信息
美国式“派糖”有何弊端?中国走向共同富裕有四段必经之路
2022-03-01 09:59:16
核心提要:
1.共同富裕是二战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想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,区别在于各国通过怎样的政策和机制,花多长时间来实现。70多年来,中国也向着这一目标在不断努力和实践。
2.新冠疫情使得全球各经济体产生了新的贫富不均,其中美国尤为严重,靠发钱不能治本,还会带来更多问题。另外,一个对外开放程度很高的经济体,如果因为疫情长期处于边界封锁,其GDP增长必定会受到和平时期中最严重的冲击,香港目前就是这个情况。
3.中国内地也有自己的问题,沿海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发展不错,但还有广袤的农村和偏远地区,有人刚刚才脱贫,有人既没有储蓄也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,更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卫生、教育等基本福利。要实现共同富裕,中国需从四大政策领域着手,一是先把收入最低的绝对贫困人员扶起来;二是解决农村户口的公共卫生系统和公共教育系统的基本资源扶持;三是人口严重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巨大压力问题;四是为自然资源接近或已耗尽的地区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。
4.以人为本实现共同富裕,首要问题是保障公平教育。中国人口数量庞大,要把公共教育系统办好,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支持都要跟上,保证落后地区师资队伍的教学水平。
5.中国基尼系数在世界排名靠前,收入差距较高。有一些巨大的财富流动,没有数据记录。第三次分配加大税收调整,需制定遗产税和房地产税。而建立一套良好税收制度的前提是,涉税信息必须全面透明。
丁教授,您好!“共同富裕”和“第三次分配”这两个词,近来大家听得比较多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通过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,成为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这个阶段性目标是否已经达成?您是如何理解“共同富裕”的?
共同富裕:七十多年 几代领导人的目标与实践
丁学良:实际上在我的记忆里,第一次听到关于共同富裕的概念,还是在1949年以前。
那时候,毛泽东在为新的国家体制建立建国大纲。大家跟不同的党派在协商,包括民族资本家党派,其中周恩来起了非常大的作用。毛泽东当时提出来的目标,就是我们以后建立起来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是要共同富裕,这是我小时候听说的。
第二次听到这个口号是1985年,是我到美国的第二年。当时把我们留学生代表召集起来,到纽约中国总领事馆学习邓小平讲话。改革开放初期,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,这是必经之路,这样才能刺激生产力,提高经济效益,走向市场经济。当时邓小平讲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共同富裕,这是我第二次听到。现在是国家第三次提出了。
“共同富裕”的愿景如何实现?
丁学良:共同富裕是一个理想境界。可以说它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,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共同愿景。区别就在于通过什么样的法律、政策、机制,花多少时间来达到共同富裕。
当然怎么衡量共同富裕,在经济学上也有很多的争议。比如说,联合国采取的就是人均每天1.9美元的购买力。但我还是相信另外一个指标可能更靠谱,以前发展经济学家用得很多,就是把一个社会最低收入的人,每天获取的食品换成卡路里。这项数据对于统计赤贫群体特别靠谱,因为世界上很多地方物价差别太大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共同富裕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很多的国家独立了,从殖民地解放出来,所以都想要追求一个长远的理想社会。但实现的过程是非常艰难,因为它需要一个社会里的经济政策,法律制度、社会政策、行政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努力,同时要经过漫长的时间,且不能够出现剧变的情况下,才能够稳步实现的目标。
丁学良:实事求是地说,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,在共同富裕这方面,以前也做过一些政策调整。
我们做研究的都知道,2002年,当时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调整。一个是要改变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别过大的现象,主要是东南沿海和西南、西北地区的对比,特别是西北地区;第二个是要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。这两种差别有重合的地方,也有很大的不同点。所以从02年开始,中央政府花了很多力气去解决这两种贫富差距。
你刚才提到的疫情是一次非常特殊的情况。在2020年年初,全世界没有几个人能预见到这次疫情的覆盖面,影响面这么大,时间拖了这么长。后来还出现变异,现在已有“德尔塔”等好几种变异病毒,而且不能保证以后不会出现其他新的变异毒株。
在此情况下,即便是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,或者是中国香港,东西方这些已经非常发达的经济体,遇上此次疫情,也产生了新的、严重的贫富不均,当然这是暂时现象。
“派糖”惯性须改变 加强扶贫谋发展
暂时解决这一现象的办法有很多种,包括“派糖”,也就是临时的发钱。美国已经发了几次钱,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:“糖”发多了以后,很多人不愿意上班,因为上班还冒风险。
现在美国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状况,就是疫情的恢复过程中,经济在疫情中的反弹力度,超过了去年4月份美国所有重要研究机构的预期。包括用新的技术,比如信息技术,大数据等等,它的反弹力度之大是惊人的。但奇怪的是,这一次反弹,GDP的增速和就业的增速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,就是因为美国政府“发糖”发多了。以至于有些州政府不得不暂停“发糖”,再发下去以后更多人不想上班了。但是也有一些州说还不行,说我们这个州的情况特殊,可能还要州政府想办法搞钱再次“发糖”,这是美国。
所有西方发达经济体中,美国社会的贫富不均最严重,但同时它又是一个高科技蓬勃发展的经济体,这其中给我们预示了什么?
如果一个经济体在过去10-15年左右,有新技术带来的新经济增长点,这个经济体将会迅速出现一些新公司,新创意,新的商业方式,以及快速富起来的一小部分人 。这些富起来的(人),可以讲是白手起家富起来的,只要搭上了高科技的火箭。
在这一点上,中国内地倒是跟美国有点像,尽管不是完全相同。但美国经济又预示着什么?
在这次疫情中,美国社会有非常深刻的自我反省。就像我所讲的,美国这个最发达的经济体,有两个很严重的问题。第一个,美国永久居民中,包括拿绿卡的人,有常年医疗保险的人数,始终是个大缺口。而这次疫情,恰恰就展示了一个社会里最重要的一些基础设施,就是它的公共医疗系统。
第二个,因为美国社会是个移民社会,新去的移民,往往都是从最底层开始做起 。这给美国带来 “劳动力红利”的同时,也产生了半个世纪未能解决的难题——美国社会里第二次分配力度较小,就是我们讲的社会福利较少。当然这是与西方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,跟亚洲相比它是不少的。比如说它(的社会福利)比香港要好,但是又没办法跟北欧比,更没法跟加拿大比。
美国不少本土白人,都有这样一个退休计划:年轻时在美国好好打拼赚钱,退休以后赶快移民到加拿大。就是因为加拿大的公共医疗设施很好,社会福利也好。加拿大的退休金,以及出现了严重经济灾难以后政府的扶持力度很大。
在这一点上,我觉得亚洲的发达经济体,尤其像香港,真的要好好反思自己: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最严重的冲击是什么?
一个对外开放程度很高的经济体,遇上了疫情这样的情况,如果长期处于边界封锁,它的GDP增长就一定会受到和平时期里最严重的冲击 。香港就是这个情况。
过去十几年来,我们有一个说法,就是说中国香港这个经济体已经太发达了,主要是靠金融业(包括国际金融业),以及房地产业。这个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,但也有很大的误差。
但另外一个现象我们千万不能忽视,从就业角度来讲,香港在就业总数中占比最高的,不是这两个行业。比如说跟旅游、服务业、零售业有关的,所有这些相对来讲低附加值,但是在就业方面影响力极大的产业,因为疫情(缘故)基本上一蹶不振,这很严重。如果说要“发糖”,要发到什么时候?
中国内地当然也有自己的问题。最重要的几个沿海城市、大中城市基本上做的还是不错。但千万不能忽视我们还有广阔的内地,还有刚刚才脱贫的那些人。还有人既没有储蓄,也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,同时也享受不到城市里已有的那些基本福利,包括公共卫生,子女教育……这一次中国内地至少要从4个大的政策领域里着手,才能够把共同富裕、共同理想主义的目标,扎实、平衡、平稳地往前推进。我想这是大部分中国人希望看到的一种前景。
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着手的四大政策领域
丁学良:第一个政策领域,在2020年时经常提到,就是对社会里常年收入最低的绝对贫困人员,一定要先把他们从底层扶起来。
过去20多年来,已经有很多人渐渐实现了脱贫。但不可避免还是会有人因为各种原因陷入贫困,或者返贫。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总数巨大的国家里,即使这部分人只占5%,总数也是非常之多。
这个群体的人数怎样测算?我还是赞成用两个指标。第一个指标,就是平均每天自己可支配的收入,而不是人均GDP。人均GDP跟个人可支配收入之间有很大的差距;第二个指标,个人可支配的收入,在他所生活的地方,每天能够给他全家每个人带来多少卡路里,这关系到人的健康和寿命。
第二个政策领域,现在我们人口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是农村户口,他们享受不到两个最基本的人力资源扶持,一个是公共卫生系统,另一个是公共教育系统 。
公共卫生系统不是指那种高精尖的(医疗)。目前一些大城市里,高精尖的医疗设施对一部分人来说很重要。但对整个国民而言,更重要的是(治疗)那些常见病、传染病、多发病、慢性病。国家三分之二的人口要么享受不到,要么享受一点点,这个基数是非常巨大的。
另外就是公共教育系统。美国的两个发展经济学家,他们去年写了一本书叫《Invisible China》,在学术界引起很大讨论。这本书讲的是,过去国际上观察中国内地,往往目光只看到了发展最快的沿海大中城市,最远也就是成都这些中部比较兴旺的地区,而没有看到广大的农村和生态非常脆弱的地区。据他们测算,在这样的地区里至少有6000万到7000万的孩子得不到公共教育系统的扶持。
农村孩子的父母很多都到别的地方去打工,带他们的爷爷奶奶又没上过学,也没办法教他们。这些孩子接受不到公共教育,他们以后会怎样?如果说把边远地区、农村地区全部算起来,可能要涵盖好几亿人,他们是属于收入的中下层。中国内地要从中等收入陷阱往上爬,如果这一部分人不能跟着爬,将永远爬不上高收入的层次。这是第二块政策领域。
第三块政策领域,也是我现在越来越担心的,中国人口严重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的巨大压力 。2008年奥运会刚过,清华大学有个很重要的项目,由当时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长李强带领,研究中国社会里面的社会流动,从70年代末以来的30年里发生了哪些变化?当时讨论完青年的上学就业、中年人的二次就业,以及农民工进城问题之后,当时大家问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,中国城市里公积金、退休金这一块,能不能在10年以后真正地起到作用?
现在15年过去了,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对这方面看得很清楚:不管它们以前有多富裕,一旦进入了老年化社会,养老金是对公共财政最大的一个负担。而中国内地已经进入了这个门槛,未来的10年或15年可能会出现一大批的贫困退休人口。
还有第四个政策领域。那些原来靠着天然资源,有了基础产业的城市或地区,比如说采矿业,基本加工业等等。现在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接近或已经被耗尽,它们有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?
很简单,东北就是。疫情之前,我每年都要去东北考察。最早的一次是2010年,考察东北的老工业城市衰落以后该怎么办。这个问题在全世界最早工业化的国家(都很突出)。英国当时这个问题最严重,当时撒切尔讲要解决“生锈的老工业带”的问题。而中国内地生锈的老工业带除了东北以外,还有西北,比如甘肃兰州、重庆这一带都是老工业带。所以我觉得至少这4个重大的政策领域,将是走向共同富裕必须要重点关注的。
以人为本实现共同富裕 首要问题保障公平教育
丁学良:内地的教育水平,在我们小时候普遍较低。但同时,对一般家庭普遍不构成负担。只要能考上,不管是考上哪个学校。我当年考上复旦大学,从安徽很穷困的县城去上海,在工厂当学徒拿的工资,还不够研究生在上海的最低生活费。复旦还补贴了我一个月几块钱,我印象深刻。
但从90年代初开始,内地教育开始急剧引进市场化的要素,其中有一些部分是很好、很合理的。
比如说在90年代初期,中国政府并没有庞大的经济和财政资源来支持快速地发展教育。同时政府又能够提供全面的公共教育资源,说句老实话,当时也没那么多钱。引进一部分市场的要素是合理、必要的,也起了一些作用。英文有句话翻译过来是“比好更糟糕的是最好”,意思是说一个好的政策,推进到一定程度以后,它一定会带来弊病。这个时候就要纠偏,同时也要协调发展。
中国人口数量庞大,要把公共教育系统办好,不仅仅是一种哲学式的结构化,更重要的是经济和财政的支持。也不是说只办好几所重点大学或者中学就行了,而是要尽可能全面地提供公共教育的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 。
人力资源非常重要。2005年我曾参加过一个教授志愿团,从北京出发,带领一帮在读的硕士研究生,趁着夏天去到中国最贫困的地区。干嘛呢?不是去教学生,而是去教那里的教师。那些地方的财政资源很低,人力资源更差。稍微有点本事的、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都不大愿意去。就算去了也留不住,最后都被沿海地区吸引走了。所以那些地方的学生,平时没什么书可看,也没有公共图书馆,更没有机会到城市里去。那时候电脑还不普及,教师水平也很差,他们本身教了10年、20年以后,没有机会得到知识更新和能力提升。
现在需要把这个问题在国家层次上提起来。我非常希望,政府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以外,也对广大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给予财政的两个支持,即资本的支持和人力资本的支持。我非常希望除了给钱以外,还能给那些地方广大的教师群体,每隔3~5年一次进行轮训的机会,这个轮训机会对提高教师(水平)非常重要。
在美国有很多这一类的大学生志愿团体。比如有一个机构叫Teach for America(为美国而教)。当时我在哈佛大学当讲师,有好几个学生都去做志愿者,到美国最糟糕的学校去。
像这些做法,一方面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调整,另一方面也要看其他国家用什么方式来解决问题。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,中国遇到的这些障碍、困难、压力或难处,在其他早先发展起来的国家里,已经或多或少遇到过。他们用什么办法来调整?我想这些才是目前中国研究和制定政策的人最值得关注的。
实现共同富裕: 区域发展、城乡发展、收入分配三管齐下
又举个例子,“第三次分配”的概念,从经济学意义和法律角度严格来讲,只有前两次的分配,牵涉的面积最大,就业市场和收入市场。不管市场化程度有多高,应该逐步制定最低时薪的法律规定;现在反对“996”,要减少出现过劳死,也该建立每周的总工作时长不能超过多少小时(的制度);还要建立逐步延长退休年龄的制度,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。
还需要建立怎样的制度?这个问题也是以前我们做调研时非常关注的。中国社会进步以后,发展的阶梯性特别明显。国外有种说法,现在中国沿海城市像欧洲,内陆边远地区却像是到了非洲,这当然不行。我们现在也就要缩小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别,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。
现在我们人口中40岁以下的人,很多要被迫职业调整,要找第二份工作。一份工作不足以养家糊口,需要打第二份工。而所有系统都牵涉到人力资本的提升和更新,这并不仅仅是个负担,其实也能带来新的产业。
第三次分配加大税收调整 涉税信息需全面透明
丁学良:我们的目标是理想化的。现在国外一直就讲,中国内地老早就该建立两种税收法:第一个是遗产税,因为遗产税如果不建立起来,那些“富二代”、“富三代”不愿再干活了,导致起跑线上就出现了巨大的不公平;第二个要建立房地产税。而且建立一套良好税收制度的前提,是经济信息必须透明、公正和全面。
以前我身边的美国人最大的抱怨是,在美国所谓的中产阶级,白领阶层最倒霉。因为他们的工资都是在电脑上记录,不能逃税,又不能漏税,所以他们永远是三明治中间的那一块,被上下挤压。其实这是人类社会的通病。比如说现在在中国内地,我每一块钱电脑上都有记录。
但是还有一些巨大的财富流动,电脑上反映不出来。我看到另外一个数据,是不久前国际学术界讨论的,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,是百分之0.46~0.48之间。
然而清华的李强教授做了一辈子(研究),他(得到的数字)都比这个高。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数据更叫人吃惊——财富,积累的财富、家里的财富、遗产的财富等等,比收入的要高很多。因为没有遗产税、房地产税。而要进入这样的税收体制,非常之难。信息必须尽可能地全面和透明,否则绝对不可能建立一套很好的税收制度。